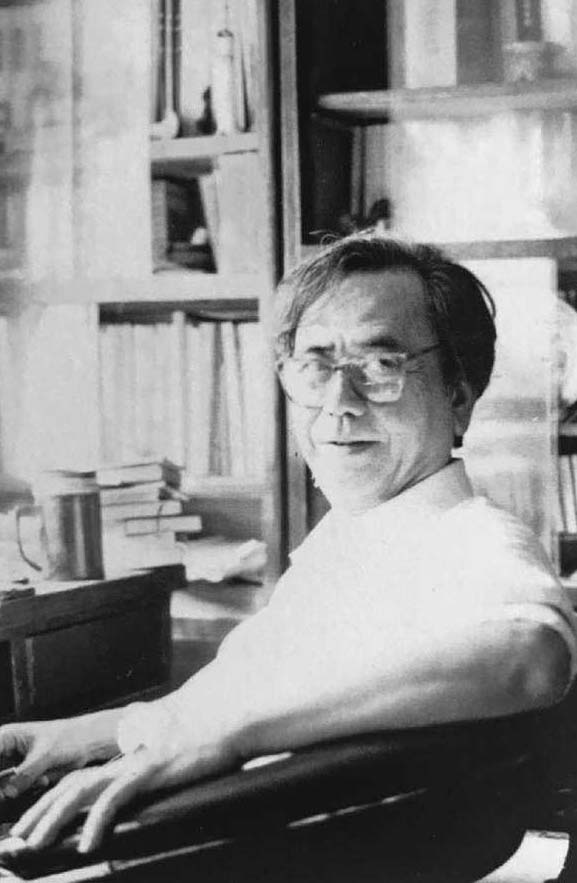1985年,林树中被聘为美国有密西根大学客座教授,向大洋彼岸的学子讲述中国绘画史。在此一年多的时间内,林树中到美国多所大学讲学并考察了美国大学的美术史教学,参观各大博物馆藏画;之后的1986年,他又到日本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访问讲学,参观各大博物馆,与美、英、日、德等国著名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这是林树中治学生涯的又一重大转折点。通过这段客座访学的经历,他的视域扩大了,注意到中西文化传统的特点并进行比较,思考如何运用西方的方法论等的治学和教学方法,择其可用的优点运用到中国美术史学科建设中来,改写中国美术史,改进教学包括研究生的培养。而之后的国宝寻踪之旅,也正是通过这次赴美讲学拉开序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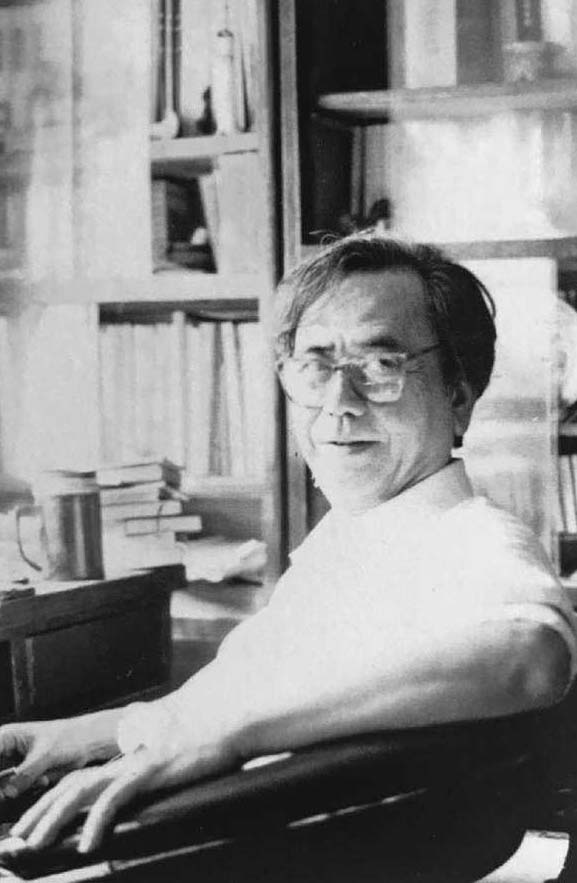
1984年赴美前在家中留影
这次访学,其渊源来自于1980年后林树中与多位国外学者的密切交往。此前,他曾多次陪同艾瑞慈教授夫妇就沈周的相关研究考察过苏州一带,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事实上之后林树中赴美讲学的具体内容,正是“吴门画派与沈周”;到了1984年,林树中于5月10日参加了在安徽合肥举行的“纪念弘仁逝世3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术界举办的首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国际学者除了密西根大学的艾瑞慈教授外,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居翰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方闻教授、弗瑞尔美术馆傅申研究员、威廉学院郭继生副教授等。除了会议期间的交流探讨,林树中也通过这次会议与国际上这些美术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学者建立起了联系。

2008年美国密歇根大学艾瑞慈教授收到林树中著作
到了1985年下旬,林树中正式前往美国,展开了这段为期一年之久的访学之旅。他曾撰写专文《访问美国、日本、香港的讲学与读画》,发表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1990年第1期,记录下了这一年在美国期间的点点滴滴:
那是1985年美好秋天的9月21日,一向被称为“老夫子”的我,第一次穿了西服踏上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座机飞往芝加哥。飞行第一个停靠站是日本东京,换乘飞机后便横渡宽阔的太平洋。因为地球是自西向东转,我们的飞机却从相反方向前进,因此感到黑夜很短,而且在时差上多获得一天的时间,到芝加哥再转机,到底特律还只是22日的下午。年近古稀的艾瑞慈教授夫妇,亲自驾车到机场接我,等到达密西根大学(或作密执安大学)所在地安娜堡时,已经是万家灯火了。
刚到安娜堡的一个来月时间,主要是熟悉一下环境,适应西方的生活方式,并作一些科研和讲学的准备工作,学校为我配备助手等。
10月7日,应郭继生博士之邀前往麻省威廉学院。第二天便由他陪同到达波士顿,参观著名的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该馆的亚洲艺术部主任吴同先生接待了我们。波士顿博物馆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它的收藏和陈列是具有世界性的,这里陈列的主要是西方的艺术品,但也有很丰富的东方(包括中国、印度、日本、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文物与艺术品。然后访问哈佛大学,并参观了福格博物馆和其他各个博物馆。11月15日前往纽约,这一繁华的大都市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我的目的主要是参观访问博物馆和与业务有关的大学。在这里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教授晤谈,我和他在一年前安徽召开的纪念画家渐江的学术会议上相识,也接触了在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一些研究生。在纽约还参加了一次某画廊举办的艺术家招待会,碰到南艺校友吴毅和沈蓉儿,大家见面很高兴,只是时间匆促未能细谈。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十分丰富,很多中国古代名画还是第一次见到真迹。再回到威廉学院时,承艺术史系主任的邀请,作了一次谈中国书画的讲座。听讲的大多是碧眼黄发的美国学生,郭博士当了我的翻译。在课堂上我还“当场表演”——书写各体书法,还画了国画,这些洋学生们感觉十分新鲜,也有很高的兴致,但也使我感到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了解很少。
回到安娜堡后,我便着手准备关于沈周与吴派绘画的讲稿。密西根大学美术史系是美国著名的资料中心,大学图书馆的东方部占有大楼的一层,收藏大量中文图籍,有不少是善本,还有台湾出版的书。美术史系的资料室、图片、幻灯片室占有一座小楼。收集的幻灯片有几十万张,可贵的是藏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全部中国古代绘画的照片。因为在南京前中央博物院收藏的古画精萃几乎全部被国民党运到台湾,所以这是研究元代及以前的卷轴画是极为宝贵的材料。在这里还看到很多台湾学者写的有关中国美术史(主要是绘画史)的著作和论文。
刚辞去美术史系主任的艾瑞慈教授,很热心于中国美术史的科研和教学。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便来中国,为抗战做了不少切实的工作,继而进四川大学从事考古学和文字学的学习,后来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沈周的绘画。1983年曾与他夫人林维贞女士(林语堂侄女)来中国考察美术史迹一年,以后又多次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著有《沈周的绘画》及有关宋代绘画等多种。
我的这次讲课对艾瑞慈教授来说真可以说是“班门弄斧”了。主要是对研究生讲的,重点是关于沈周的家世家学及前期的绘画。由武佩圣博士担任翻译。
安娜堡所处的纬度相当于中国的长春。很早就飘起雪花,寒冷的时间很长,春天来得晚。到1986年2月28日我应堪萨斯大学美术史系李铸晋教授的邀请前往堪萨斯大学时,还穿着夹层大衣,这次因有助手卢素芬的陪同,生活上得到很多照顾。堪萨斯城的地理位置正好在美国的中心。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就在市内,我们是先到纳尔逊博物馆参观三天,然后去堪萨斯大学的。这个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绘画、雕塑等很著名,东方部主任何惠鉴先生是个美籍华人,学问渊博,风度不凡,看画和学术交流,获益良多。我在堪萨斯大学讲的《关于沈周研究的新发现》,由李教授亲任翻译。这里中国大陆和台湾来攻读学位的美术史研究生有好几位,他们学习勤奋,成绩很出色,如北京去的万青力能画能写,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只是中国去的研究生,英语听写水平都嫌不够高,使深造碰到一些阻难。
3月1日,离开堪萨斯前往圣路易斯,有博物馆的东方部主任欧阳国兴先生来接。欧阳先生是艾瑞慈教授的高足,陪我们游览市容和有特色的虹形大铁桥等,然后参观博物馆。随后还到华盛顿大学吴讷孙教授家作客。吴教授是研究董其昌的专家和作家,承他赠送研究董其昌的著作并交换了意见。这次旅行收获很大,心情也很愉快。
4月巧日,在密西根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作“上海画派与任伯年、吴昌硕”的学术报告,由游露怡博士翻译。听众都是密西根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他们对任伯年和吴昌硕的画很感兴趣,讲完后,还要求把幻灯片再放一遍。美术系的学生还画了速写送给我留念。下一次在美国的重要旅行就要算与美术史系的研究生们前往纽约、华盛顿、波士顿之行了。
到波士顿和纽约都是第二次了,但感受更深,收获也比第一次为大。印象很深的是刚下飞机进入波士顿在一家饭馆吃饭时,店主人听说我是从中国来的,特别邀我在他的留念簿上签名;又听说是从南京来的,还要我拿颗图钉在墙上挂的世界大地图上找到南京的位置钉上,地图上已经钉了很多图钉,店主的热情真是难得,这也说明从中国来的人受到美国人民普遍的尊重。
在华盛顿,住在一个研究生Ingrid Larsen的家里,她的父亲是个政府的中级官员,住处、生活条件都很好。她拿出一本厚厚的在中国旅行的照片本子给我看,并夸中国是个美好的国家,还陪同我游览华盛顿广场,总统府、历届有贡献的总统纪念馆、最大的教堂等地方。
夫瑞尔博物收藏中国古代名画很多,馆长罗谭先生热情接待,东方部主任傅申博士要算是老朋友了,把馆藏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绘画差不多都拿出来,供我尽情观赏,临别还赠送幻灯片,真是盛情可感。
在美国期间,还由艾瑞慈教授、武佩圣博士等陪同参观了克里夫兰博物馆、芝加哥博物馆、底特律博物馆等,至于密西根大学的艺术博物馆(武佩圣先生是该馆东方部主任)更是配合教学差不多每周要去一次。
其他时间还在美术史系听艾瑞慈教授关于吴派绘画的讲课,研究生的论文汇报式试讲,辅导研究生(也是我的助手)卢素芬关于《曾鲸肖像画研究》的论文。此外则进行日常的研究工作,撰写长短篇文章,拍摄幻灯片,补习英语等。
在快离开美国之前,还应美国友人麦克先生之邀到密西根湖周围游览。密西根大学的安娜堡地处五湖之间,风景优美,是旅游的好地方。之后还到农村参观旅游,了解风土人情。缺憾的是原拟在回国时途经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停留,因值学校放假,高居翰教授不在学校未能成行,但高居翰教授其后多次来中国,并到南艺讲学,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很多的。
在美国一年,接触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文化的诸多方面,感受新鲜,也是深刻的。这常促使我思考一些问题。其中思考最多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比较。
长期以来,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各自发展成自己的体系。从生活方式、思想方法、价值观念等等方面,总是有那么多的不同。作为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学者,对于美国海滩、湖滨男女的过分裸露、大街上的拥抱接吻,也许感到不习惯。也在纽约的大街上看到与花花世界对比强烈的行乞流浪者、盗窃、卖淫、赌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很复杂的。对于西方现代派的绘画、雕塑、音乐等,开始总也觉得不很理解,但是接触多了,经过思考,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认为西方艺术的发展有它自己的土壤、气候、人为的因素,是合乎它自身发展的规律的。我们应该通过思考、选择,吸取他们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来充实和发展自己。但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有我们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否定自己的一切,全部照搬西方,显然是不对的。我是主张中国画要改革的,怎么改? 完全改变国画的传统去适合西方人的胃口吗?这也不对,我们还要把自己的双脚站在中国的国土上。关于这些问题实在是纸短话长,且留待以后细谈吧。

1985年在日本国立京都博物馆前留影
1986年8月26日,林树中离开美国来到日本,展开了为期十天的日本访学之旅。在日本期间,林树中得到京都国立博物馆资料管理研究室室长西上实先生、金泽工艺美术大学远藤光一教授和留日工作的沈伟先生的大力帮助,并会晤了东京大学的铃木敬教授、户田祯佑教授、小川裕充教授,京都大学的岛田修二教授;参观了国立东京博物馆、京都博物馆、大阪市博物馆、大和文华馆、泉屋博古馆等博物馆,主要是看收藏的中国古代画。同时,游览奈良的法隆寺、药师寺、东大寺,兴福寺等,观摩其建筑、雕塑、壁画等;还在东京博物馆为日本美术史协会东京支部作了一次学术讲演。
其后林树中又到香港两周,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了一场讲座;并与饶宗颐教授、文物馆馆长高美庆博士、出版家许礼平先生、画家刘国松先生及《大公报·艺林》主编马国权先生交流会晤;饶宗颐教授还为其担任了讲座主持。他在文物馆看了很多馆藏画,又访问香港大学,与艺术系主任时学颜教授等进行交流。在参加饶宗颐教授的70寿诞会上,林树中还巧逢正在香港停留的南京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刘海粟老人及其夫人夏伊乔女士。此外他还结识了香港美术专科学校校长陈海鹰先生和其他学术界人士。经高美庆博士的介绍,他还观摩了冯平山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历代名画以及其他私人藏画,又到著名古董街 摩罗街的多家古董店观摩名画。

1986年访美归来后全家合影
林树中自从出国讲学以后,其治学和论著都有极大转变。其中一个显著的方面在于,他积极运用西方的方法论治学并以此教育他的学生。美术史研究方法论是近些年来愈来愈为国内学者关注和重视。而林树中于访美讲学期间,在和艾瑞慈、高居翰、方闻、李铸晋等海外同行的接触中,强烈地意识到方法论的重要性,回国后还专门发表了题为《中西美术史研究方法之比较》的演讲。林树中认为,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互相联系,交相辉映,研究者不但可以跨越国界的限制,还应贯串不同学科;西方美术史家的学科自我意识较我们为早,而且有良好的哲学思辨的传统。每经过一个阶段总有关于方法的理论反思,这也就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在这方面,只要有益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不论何种理论,都可以“拿来”。此外在之后,他积极参与到美术史论研究的国际交流当中:80年代末美国加州大学高居翰教授、英国伦敦大学韦陀教授来华访学,林树中都积极参与接待陪同并与他们在学术方面保持着长期的联系和沟通。高居翰先生还曾到南艺讲学,在学校住了将近一个星期,林树中就陪同高居翰在南京周边考察,主要内容是栖霞山、祖堂山的六朝石刻,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只有20多岁的青年教师刘伟冬;作为翻译和陪同,他全程见证了二位先生接触交往的经过,林树中以他渊博的知识和高居翰对话,而这段学术熏陶对于刘伟冬后来的学术道路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98年美国著名汉学家高居翰教授来华讲学期间在林树中家中做客(从左至右分别为林树中、高居翰、周积寅和阮荣春)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俞剑华先生较为传统甚至略显保守的态度相比,由于时代的更新,林树中的研究不仅在纵的方面做到了博古通今,在横的方面也能够尝试着去融汇中西,使之学术内涵愈加丰富。1986年旅美归来后,林树中曾作过一篇题为《中国画的“变”》的文章,文中论述的角度就涉及了“古今中外”不同的方面:
前些时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关于中国画的讨论似乎热闹了一阵子,青年人打先锋,一些中年画家或发表见解或观望,老年画家似很少公开发表言论,但私下里也是议论纷纷。总的来讲,一些青年人勇气可嘉,但是言论过激……一些青年画家几乎是完全套用西方现代派的形式来画中国画,叫人无法看懂,于是一些老画家摇头三叹,好像中国画的传统就要毁于一旦。
以上的理论似乎已不新鲜。但最近又出现一些理论,发言或公之报端的人……似乎是一个口径的要“坚持传统”。有一些画家在“保卫传统”的大旗下,一如既往,照样画他的“传统”中国画,好像是改革的阵风已过,一切都又回到老路上去。
其实,传统正如王世贞所已经指出的,是历来不断变革新成果的积累,因之,没有变革也就没有传统可言,变革也是否定之否定。但不是转圈子走老路,而是螺旋式的提高和前进。
今天在一般人看来,林树中是一位“传统”的学者——研究的对象趋于传统,研究方法上也从来不标榜“新潮”。但从这些文字来看,他的思想却并不保守——在坚守传统和积极创新这两方面而言,他甚至更加倾向于后者。当然从整体上,他的观点是全面而辩证的。也正是有了对于“古”“今”“中”“外”间关系的整体把握和认识,他才能更好去驾驭自己所做的传统部分的学术,不至于落入固步自封的桎梏。